舌尖之上,味覺之中,其實也可以有故事,甚至是一種混合著記憶與故事的難忘滋味。
近年來各種有關《燕行錄》的專書紛紛出版,從各種角度環視著《燕行錄》所能提供的特殊視角,協助研究者們重新審視著明清歷史的各種幽暗伏流。但是除了嚴肅的學術方向外,事實上《燕行錄》也能夠有不同的讀法,例如味覺感受與歷史記憶,以及文化理想的東亞跨國流轉。
換一個角度,我們便能發現文獻中的言外之意。舉例來說,明清北京城街邊小吃會是什麼樣的滋味,當時的外來旅人們究竟留下了什麼樣的旅行食記,而這些唇舌間的滋味在當時是如何與異國旅人產生了情感的聯繫,甚至是一種歷史記憶上的互動。這原本是極難回答的問題,但歷史研究的有趣之處,往往是在換一種研究視角來重新理解某一種的歷史文獻所提供的重要訊息,並且解讀出一種特殊的時光記憶。
Image may be NSFW.
Clik here to view.
【十八世紀描繪朝鮮出使北京旅程的《燕行圖》】
圖片說明:十八世紀前後朝鮮畫師筆下描繪朝鮮燕行使節的《燕行圖》,作者不詳,研究者推測可能為金弘道的作品。該畫作收錄於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的《燕行錄全集》。
明清時期北京城的街邊美食口味,並非完全沒有留下記錄。
朝鮮使臣們在使節出使記錄文書《燕行錄》裡提供了一扇窗口,使我們得以一窺當時的飲食記憶。對於北京城的飲食,朝鮮使臣們以為「大抵飲食之味,多淡而少濃」,若和現代人的感受相比,這種感受看來是和現代的北京口味有所不同。
或者,朝鮮使節的口味更重,北京城各色飲食不夠濃厚,也沒有熟悉的家鄉醃造醬菜配合佐飯,想來可能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吧。
總之,若是換一個角度來看,《燕行錄》其實不只是一種使節文書,也可以是一種另類特殊的「旅行食記」。朝鮮使臣們的筆下不只有軍國大事,他們同時也記憶了食物的各種滋味,同時也記憶了皇明與朝鮮的關係,表達出他感情上「或存或亡」的意識。燕行使節團歷代前輩們留下的有關前朝的飲食記憶文字,讓後來使臣們,在字裡行間有了一種無奈與遺憾的特殊心靈感受。
Clik here to view.

【圖片說明:朝鮮著名畫師金弘道(1745~?)筆下描繪使節團出使活動的《燕行圖》之一,描繪的是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該圖現藏崇實大學韓國基督教博物館。】
時至今日,透過國際學術出版的合作,原本藏於東亞各國的《燕行錄》才有了與讀者見面的可能性。存世的各種《燕行錄》,數量相當驚人,裡面恰恰包存了朝鮮使節們昔日出使北京的「飲行食記」。其中,日本學者夫馬進教授與韓國學者林基中教授合編的《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這部書中就收錄一段很有趣的文字記載。
食物則捲煎髓餅、沙爐燒餅,羊肉肥麵、角兒糖、沙餡饅頭、巴茶蜜酥餅、肉酥油糖蒸餅、盪麵燒餅、椒鹽餅、羊肉小饅頭、細糖王芠、白千層蒸餅、酥皮角兒糖、棗糕、芝麻燒餅、日(熱?)捲餅、爊羊蒸【食卷】、雪糕、夾糖餅、兩熟魚、象眼糕、酥油燒餅、糖酥餅,此等皆自皇明流來食物,而於今或存或亡。觀於尋常佐飯之具,則沉菜及炒豬肉、熱鍋湯是恆用也。柔薄兒以麵造,及[類?]我國霜花,而皺其縫,此蓋饅頭之屬也。其餡以豬肉和蒜為之,餅餌中最佳類也。又以麵餅,煎以豬羊油,輕脆易碎,殆似我國之江丁,其善造者,和糖屑納其中。又以粘米作小圓餅,浮水烹之,乘其熱而啖之,此又稱好味也。大抵飲食之味,多淡而少濃。
朝鮮使臣們在此次的出使記錄中,提到北京城中習見的各種美味可口的甜鹹麵類點心,像是燒餅、酥餅、蒸餅、捲餅、千層蒸餅、棗糕、酥皮角兒糖、夾糖餅、象眼糕等等,這些食物在使臣們的眼中都是自「皇明」(明朝)以來即有的口味,但改朝換代後,而今或存或亡。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小甜點、小麵點,卻是和明清鼎革,改朝異代的歷史記憶有著深刻的關連。飲食之際,舊時人物或者也如這「皇明口味」一般,現於今或存或亡,徒留追憶吧。
使節們在文字裡提到北京城裡的一般人家,平日多半是食用「沉菜、炒豬肉、熱鍋湯」,還有用豬肉和蒜末作餡的麵點「柔薄兒」。想來或許和今日北京飲食中的葷素熱炒、還有豬肉包子,有一些歷史上的淵源吧。至於「粘米作小圓餅,浮水烹之,乘其熱而啖之」則讓人想到了糯米湯圓,也是在寒冷冬日中暖人心脾的好滋味。時至今日,這些點心也在北京人們的生活中出現,這些都是讓人記憶這座古老城市的生活美味。
Clik here to view.

【朝鮮文人畫家金弘道《燕行圖》之一,描繪燕行使節團的人馬隊伍】
圖片說明:朝鮮著名畫師金弘道(1745~?)筆下描繪使節團出使活動的《燕行圖》,現藏韓國崇實大學韓國基督教博物館。
庶民小吃食中的思明情懷之外,朝鮮使節們另外的一種特殊飲食風尚,便是找一些前明故人的後裔一起家宴飲酒,一方面敘舊,另一方面便是想從這些人的口中,得到一些關於清朝的切實情報。
從《燕行錄》的記載中,我們常見到使臣們每次都會在使行途中詢問前明文人谷應泰的後人所在,使節團多半會過訪谷家,好好飲酒筆談,交流一下感情。例如朝鮮使臣李商鳳(1733-1801)便在其燕行日記《北轅錄》中,記錄了他曾與谷應泰的後人親族在飲宴席間的筆談。飲宴之間,他們曾談論到谷應泰的名著《明史紀事本末》,言談中流露出其對明代史事遺獻的興趣。
李氏在與谷氏後人親族的對話中,也談及了明清衣冠制度上的敏感問題,他還開了一些比較有政治敏感的小玩笑:
余曰:「爾們衣裳之制,較吾們孰勝?」曰:「貴國襲前明之服,吾們遵時王之綱,不可可否。」
這一則酒席間的小玩笑,文字的內容大意是說,李商鳳問道:比較起來,我們兩國的衣冠制度,那一邊比較優秀勝出呢?谷家後人擔心禍從口出,回答說:「貴國朝鮮襲用前代明朝的衣冠制度,我們則是照著國家當下的法律綱紀,因此對這個問題,不置可否」。
類似的例子甚多,多半發生在聚會飲宴中,清朝士人與朝鮮使臣們往往都會談到彼此衣冠上的差異,引為談資笑語。例如洪大容與李德懋曾在其燕行日記《乾淨衕筆談.清脾錄》中談到另一則有關衣冠制度的笑語,而且也記下了當時飲食聚會的當下,眾人常常聲言:「以茶代酒」,而洪大容人以為如此則「風流掃地盡矣」。
每諸人飲酒,必呼茶代之,曰:「以茶代酒,弟之風流掃地盡矣。」起潛曰:「兄衣四面俱開,亦是前明制耶?」余曰:「此乃戎服,似是明制,不敢質言。官者朝服及士子道袍,大抵襲明制耳。」(洪大容、李德懋,《乾淨衕筆談.清脾錄》,頁87。)
這一段文字中恰恰看到朝鮮人們性好飲酒的習慣,來到了中土,遇到了「以茶代酒」的交際套語,即有施展不開的啞然一笑。雖然朝鮮使臣們時常利用飲宴之際,三杯黃湯下肚後,酒後吐真言的機會,套出清朝人心中的各種時局議論與隱隱心曲,但清朝士人們也並非是省油的燈,想出了「以茶代酒」的應酬話,把這可能事涉政治敏感的失言場面,巧妙的用哈哈一笑來克服過去。
Clik here to view.

【燕行錄相關書影】
除了上述這一些飲宴中的小插曲外,千里外遠道而來的朝鮮使節們,日常飲食中最感困擾的便是水土不服的各種腸胃毛病了。這些在今日看來無關痛癢的小病痛,在醫學尚不發達的當下,常常會奪人姓命。
明清時期,來自朝鮮使臣們來到了北京,除了漫天的沙塵難以習慣之外,常見的記載便是水土不服的問題。其中又以飲用水為最,為了克服北京水質苦鹼,難以入口,使節們甚至要行賄看守館驛的兵丁門吏,才能買到適於飲用的井水,以免使節團患病難癒,客死異鄉。例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跟隨使節團奉使燕行的子弟軍官李商鳳(1733-1801)便曾在《北轅錄》一書中記錄到北京城水質偏醎,飲用上難以適應的情況:
「北京水味甚惡,如我國闤闠中最醎之水,醎味久服漸勝,而最難堪者,醎中有甘意,不忍下咽……」。
醎味水硬之外,卻又夾帶了一些甜味,的確讓人難以飲用。
細檢存世的數百卷《燕行錄》,類似記載在當時朝鮮使臣的筆下,每每躍然紙上。時至今日,讀者們透過歷代朝鮮使臣的《燕行錄》的記載,字裡行間,總讓人體會到古人出門在外獲得合適飲用水的不易,擔心飲食不適患病,以及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
Clik here to 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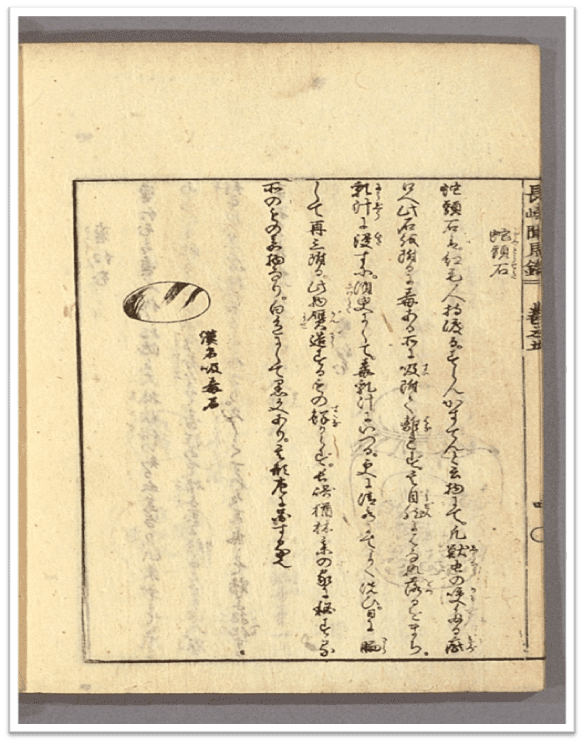
【広川獬《長崎聞見錄》有關「吸毒石」圖文書影, 現藏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如同現代人出國旅行,隨身要攜帶常備藥物一般,朝鮮使節也會隨身帶藥,以備不時之需。但多半的情況下,這些藥物多會用來在旅途中作為禮物,和沿途的官民人等作作人情,打點各種來往關係。
飲食不適而食物中毒的例子,其實在前近代社會中十分常見。因此,尋找各種醫藥與解毒特效方,也是朝鮮使節們出外查訪的重點之一。
燕行使節們特別關心一種解毒藥「吸毒石」,又稱之為「蛇頭石」,名稱甚多,但是相關的傳說更多。清代著名文人紀曉嵐《閱徽草堂筆記》中特別有一篇文字,詳述了吸毒石的掌故由來。當時的東亞各國都有相關的文獻記載提到了「吸毒石」的解毒神效,甚至耶鮮會士南懷仁也曾為此,專門以滿文譯寫下了西方醫學的相關看法。
日本江戶時代的博物學者們,也曾在記載西洋事情的著作中,留下了圖片與文字的記錄。例如:當時的蘭學作品中,江戶時代後期京都著名蘭學醫者広川獬《長崎聞見錄》(文政元年(1818)刊行)一書曾經提到了「吸毒石」的圖畫與記錄,書中將「吸毒石」稱之為「蛇頭石」。
當然,朝鮮燕行使節們也不例外,例如朝鮮使臣李宜顯《壬子燕行雜識》中便記錄了「吸毒石」等來自異國的藥物。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朝鮮使臣們為了一探這種解毒奇藥,也曾在京城四處打聽,最終在《燕行錄》中留下了相關的記載,將這些異國的知識傳回朝鮮。
從記憶前朝的「皇明食物」到尋找維生的水源,甚至是為了解毒救命的奇藥,歷代朝鮮使節們為後人留下了萬分精采的旅行食記。或許,對於《燕行錄》的這一種特殊詮釋與理解面向,也只有旅人們才能真正的明白其中的動人之處吧。
文章部分內容,曾經編輯摘節,發佈於旅飯網站